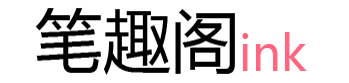于任何地方。”
云初把书本找出来,用脚踢一下坐在他前边的人。
“往前挤挤,我的腿伸不开。”
前面的太学生迅速用屁股蹭着蒲团往前挪,给喜欢摊开双腿坐着听课的云初让出位置。
云初又瞅着左边高谈阔论的士子道:“把《周髀算经》的讲义给我,你再找人抄一份。”
士子叹口气打开一个包袱皮,将一本厚厚的讲义拿给了云初。
云初一边翻看讲义,一边问道:“怎么,倭国人跟高句丽人打架了?”
士子连忙道:“是啊,就在昨日放课之后,一个叫做韩场的倭国人把一个叫做高山的高句丽人给打了,听说伤的很重,断了骨头,还吐血,就跟你上次殴打那个新罗王子一样,就剩下了一口气。”
云初瞅着那个士子道:“我这两年来总共殴打过的人不超过三个,你竟然还记得?”
士子怒道:“你每一次打人,都把人打的那么有特色的,我怎么可能记不住?
如归不是因为惧怕你的拳头,你以为我辛辛苦苦抄录的讲义就这样白白的给你?”
云初拍拍士子的肩膀,塞给他一把竹筹道:“补偿你的。”
士子闻言立刻低着头数着手里的竹筹,数完之后又伸手道:“只有四天半的量,做人就要做好人,补足五天的伙食,我就不跟别人说你抢夺我的讲义了。”
国子监里的年轻士子不多,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算学科,如果去明经科看看那些花白胡子的老头,就能知晓五十老明经是什么道理了。
刘开先生抱着一个茶壶,慢悠悠的走进了课室,一进来就瘫坐在软垫子上。
先是喝了一口油茶,然后慢悠悠的道:“听不懂的可以出去玩耍了,莫要强求,反正我今日要驳斥的是子午线“千里影差一寸”的谬论。
听懂的人呢会精神百倍,听不懂的就会昏昏欲睡,为了不打搅听懂的人,那些想要睡觉的可以回去好好睡一觉,不用在这里浪费光阴。”
云初身边的年轻士子当即起身准备要走,见云初不动如山的坐在那里,就奇怪的低声道:“你听得懂?”
云初不屑的道:“南北相距一千里的两个点,在夏至的正午分别立一八尺长的测杆,它的影子相差一寸,这个论点本身就有问题,正好听先生解惑,这有什么听不懂的?”
士子冲着云初挑挑大拇指,就潇洒的离开了,今日从云初手里获得了不少竹筹,正好去晋昌坊美美的大吃一顿,稍微弥补一下听不懂先生讲义的心。
刘开只要开始讲课,除过中间会停下里喝几口水,其余时间都会滔滔不绝,他讲课就像是有狼在后面驱赶一般,从不停顿,更不管学生们到底听懂了没有。
如果没有听懂,想要重新学习,就要重新交一次束脩,去他特意准备的小课堂上讲。
这一手本事可是家传,他父亲刘焯便是用这个办法将学问当做生意做,不向他送见面礼、或者送少了礼的,根本就得不刘焯到他的真正教诲。
不过,这一对父子虽然贪财,却是真正有本事的人,云初为了不被人家勒索,不得不凝神静气,将刘开讲述的每一个字都牢记于心,回去之后再慢慢的回忆整理。
从刘开的课堂上下来,所有的学生都如同大病一场,一个个脸色蜡黄,无精打采。
刘开在离开课堂的时候还好言相劝,希望学生们去他的小课堂听课,如此,就不用在这里受罪了。